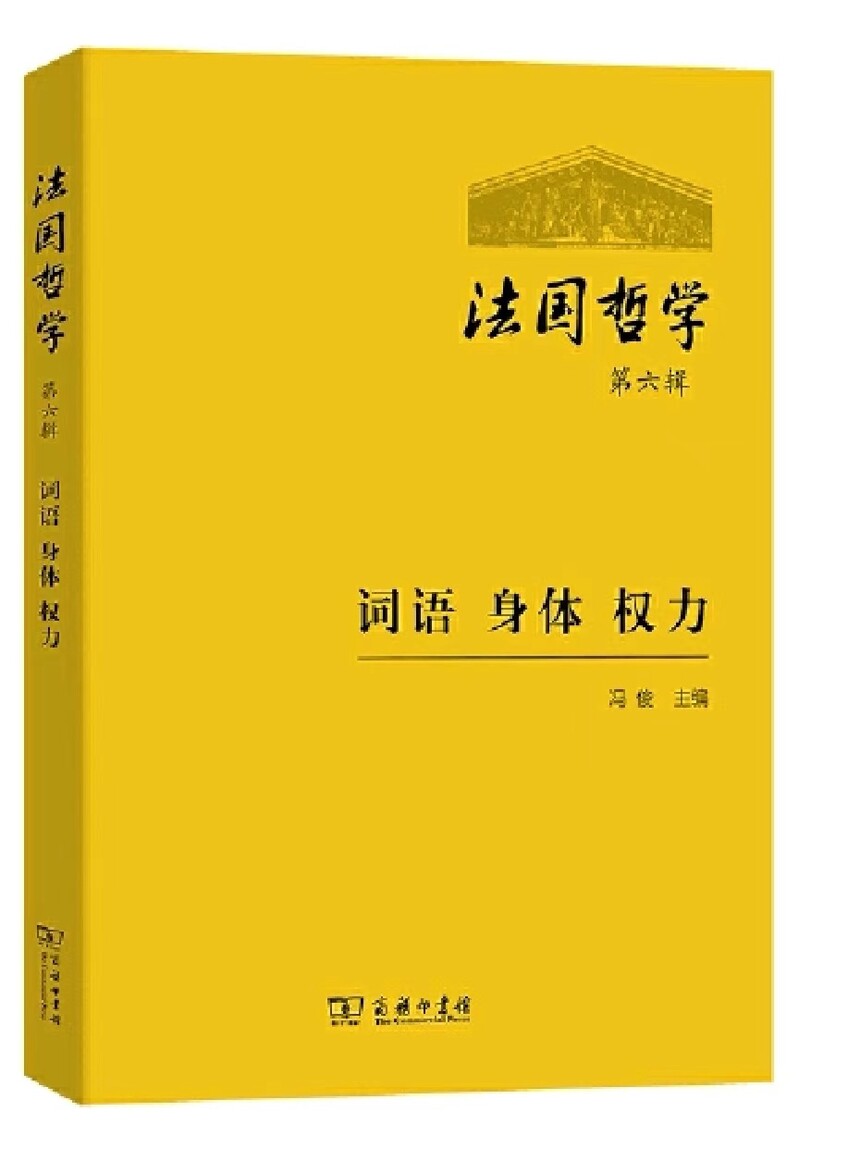|
身体与世界的世界性时间:2024-08-02 《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性”(Weltlichkeit)概念是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不是世界内诸物的集合而是此在(人)存在的建构性环节。世界的世界性(本质结构)即世界的意蕴(Bedeutsamkeit ),它让此在得以发现并使用世界内诸物。然而,从现象学的视角看,这一“世界性”概念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在考察世界现象的构成时没有把身体的作用纳入考量。此外,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我发现了一种详细的身体分析,这正是《存在与时间》所欠缺的。尽管梅洛-庞蒂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世界本质结构的概念,但他从身体角度通达人的生存现象的方法,对我们经由身体获得一个新的“世界性”概念是一个有益的指导。因此,本文试图运用他的方法论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性”概念。我的结论将表明,移动(身体)的可能性是与世界意蕴同等源始的世界的本质结构,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此外,我还将表明、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考中,如措利孔讲座(Zollikon Seminars)所表达的、海德格尔已经接近发展出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性”概念。 一 让我们从对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一个例子的考察开始:当我们看一个立方体,我们构想它有六个面,但我们从未同时看见立方体的六个面:有一些面对我们来说总是隐藏着的。我们如何构想出有六个面的立方体呢?我们拥有先前围绕一个立方体运动且连续看到它不同侧面的经验,但为了构想出拥有六个面的这个立方体,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唤醒这经验。为了将一个立方体构想为一个立方体,我们并不真正需要考虑我们身体的运动,“因为考虑已经做出,新的显现已经和曾经历的运动结合在起。并呈现其自身为一个立方体的显现”。这里,梅洛·庞蒂暗示,我们的视觉已经被围绕它运动的可能性所更改。我们在下面这句话中能够发现相似的含义:“空间被“包含”在立方体的各个面之间,就像我们被关在房间的四周墙壁之间。为了能构想立方体,我们需要在空间里采取一个位置,一会儿在立方体的表面,一会儿在它的里面,一会儿在它的外面。这样,从那一刻起,我们就能看到立方体。”对于这句话,我们只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在空间中采取一个位置,因为此位置已经被纳人我们的视觉,视觉本身已经被运动的可能性所改变。在此我们想强调,梅洛-庞蒂思考的意义在于,我们是身体化的意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能移动的身体,且我们对世界的知觉已经被运动的可能性所改变。用梅洛·庞蒂自己的话说:“意识首先不是"我思”的事情,而是“我能”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转向世界现象。我们主要关切的是世界的世界性,后者宣指构成世界整体性的本质结构。“世界性”这一概念最初来源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人)的考察。对海德格尔面言,世界现象是此在本身的一种特性,因此世界的世界性就是此在“在一世界一中”的一个建构性环节。虽然海德格尔反对把世界理解为世界内诸物的集合,他仍然认为有必要通过考察世界内诸物及其所拥有的存在来考察世界现象,因为世界作为“在一世界-中”的建构性环节,是使它们这类存在得以可能的东西。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照面的世内诸物拥有的这种存在,被称为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亦即可用性。@作为此在,我们总是操劳于这个世界,在这种操劳中,我们操作上手之物并且使用它们。当人们操作和使用这些物时,上手之物的存在就获得了最恰切的理解。在操劳中与我们照面的上手之物就是“用具”。世界中充满上手的用具。 然而,我们不能将所有上手用具统称为“世界”,因为上手的用具在我们发理其中的一件用具之前就已是一个整体。例如,一支钢笔并不仅仅是我们碰巧在桌子上发现的一个单个的用具;在它旁边,我们还能发现墨水纸、信封、涂改液、订书机,等等。这些物件是其意为“为了写”的用具整体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书写的意蕴是“为了同他人交流”,交流属于此在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理解了此在存在的可能性与上手用具之间的关系网络,此在才能领会某单个上手用具的意蕴。在这样一种海格尔称之为“因缘”的关系网中,此在把他自己的存在当成世界的“为了……",这种“为了………”在其最源初的意义上规定了世界的意蕴。从这种世界意蕴中产生了与世内上手用具打交道的意道;从与世内上手用县打交道的意蕴中产生了用具整体的意蕴;从用县整体的意蕴中,人们领会了某单个用具的意蕴。因此,世界的意蕴实际上是一个“赋义”(signifying)关系整体。而且,由于意蕴是属于此在展开状态的某种领会,所以此在总是已熟悉世界的意蕴。对“为了……”的领会意味着此在总是操心于他自己的存在,因此他总是操心于作为他自己的存在的建构环节的世界。这种振心使此在得以发现上手用具并根据其意蕴来使用它们。因此,世界的意蕴是构成世界整体性的本质结构。由此可见,世界的世界性不外乎就是世界的意蕴。 海德格尔以意蕴来理解世界性确实是正确的。没错,此在只有操心这个世界,他才能发现上手用具并依其意蕴而使用它。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面发现某物上手意指发现某物“可用”,亦即发现某物有用和可通达。有用性和可通达性尽管密切相关,但还是能被区分开来。例如,行人在马路中央发现了一块石头,石头对他面言是无用的但却是可通达的。因此,他拾起面抛之。相反,一个在事故后瘫痪的人也许还理解门、桌子和其他物的有用性,但由于它们已经失去了可通达性,因而对他来说不再上手。上手状态是有用性和可通达性的结合。某物是可通达的,当且仅当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接近、把握和操作它,这些可通达性的方式是移动我们的身体的方式。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移动我们的身体以接近、把握和操作某物,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发现作为上手用具的此物。 我们以锤子为例。要接近我们所看到的锤子,那么在我们的视觉与运动之间必须有某种对应的关系。这即是说,对锤子的视觉感知必须包含如何向它移动我们的身体的信息。因此,在我们经视觉发现任何上手之物之前,我们视觉之中的物必须已经根据我们的移动(身体)的可能性而被定位了。什么构成了移动的可能性呢?移动向来是身体的移动。我们移动的身体有许多部分,我们总是能选择移动身体的“这”部分或者“那”部分:因此,身体就是移动可能性的第一个要素。我们总是能选择朝“这个”或“影个”方向移动我们的身体的某部分;因此,方向从属于运动的可能性我们总是能够选择按既定的方向移动身体的某部分到某种程度,那么,按既定方向移动的程度亦属于运动的可能性。但移动方向和移动程度并不是移动可能性之两种不相干的要素,因为朝某方向移动的程度实际上是方向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因此,我们称二者的结合为“运动定向”(oientaton ofmoving),这是移动之可能性的第二个要素。据此看来,我所移动的身体与运动定向是构成运动之可能性的两大要素。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修选择我们想要运动的身体部分和运动定向,是因为我们向来总是将它们理解为我们的运动之可能性,即使我们实际上并未运动。它们构成了我们的运动的视见(sight)。对我们而言,它们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同意蕴一样,运动之可能性亦是属于此在之展开状态的一种领会,它是此在的一种特性。 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运动之可能性的两个要素。移动的身体有许多部分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也就是说,彼此相对地移动。事实上,仅因为我们能彼此相对地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我们才能运动。例如,当我们握拳,我们运动手的不同部分朝向波此。如果我们的手不分部分,那么像握拳这样的运动将会不可能。同,如跑步、跳水、转身和身体任何可能的运动方式都是如此。因此、运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以使其互相相对。这里的“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互相相对",恰恰就是我们业已界定的运动可能性之第二大要素,即运动的定向。因此,运动的定向由身体的定向决定。通过我们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相对地朝向某一方位运动的具体方式、这个运动定向就与其他定向区别开来。运动之定向对所移动的身体的各部分来说不是同性的,因为每一定向对身体的每部分雨言都有不同的意酒这就是我们能区分上和下、左和右、前和后的原因,它们都是身体化的定向。一句话,运动之可能性的第二个要素莫基于第一个要素之上。 现在我们已准备好讨论如何接近我们看见的锤子。作为我们总是拥有的一种领会,运动之可能性使我们能以诸多不同的方式移动我们的身体但为了接近锤子,我们的视觉必须已经被移动方向所塑造,以便我们所看见的锤子出现在我们能够朝之移动我们的身体的方向上。我们的视觉也必须被朝某一方向运动的程度所塑造,以使我们所见的锤子在某个“近处”出现。一物的“近”并不意指此物与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客观距离,而是指为达及此物我们所需移动我们的身体的程度。台灯比它后面的墙近,是因为对我们的身体而言,触及它比触摸墙更近。简而言之,我们的视觉必须按运动定向而被塑造,以使我们所见的锤子出现在某一方位,此一方位包含有关如何接近锤子的信息。更进一步说,由于运动的每一种定向都是-种身体定向,当我们在某一方位看到我们近处的锤子时,我们同时也知道如何移动我们的身体部位去达到它。例如,如果它在我们右手边的地上我们会弯腰并伸出右手去通达它。移动我们的身体部位去通达锤子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我们对它的视觉感知中。总之,为了接近我们所见的锤子我们的视觉必须已被运动的可能性所塑造,以至于我们所看见的并不仅仅是某种影像,而是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移动去通达的某物。 然而,视觉本身的本质与运动毫无关系。一种没有方向、没有远近的纯粹视觉是可设想的,如上帝的视觉。唯有身体化意识的视觉才会与运动有关,因为运动总是身体的运动。作为身体化的意识,视觉与运动的联系是生而有之的东西,但二者之间的对应性是在我们的儿童时期通过我们的运动经验逐渐形成的。有些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婴儿初次看见一个顶部有手柄的玩具时,会尝试去抓玩具的底部。对此的解释是,婴儿有关运动可能性的视觉最初是“颠倒”的;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婴儿的运动经验,婴儿的视觉被运动的可能性逐渐改变。由此,视觉与运动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建立起来,世界对婴儿变成了“正”的。然而,如果视觉与运动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打乱了,那么,即使是成年人也必须再次调整其视觉以适应运动行为。梅洛-庞蒂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这种实验的例子。实验中,实验者被要求戴一种能使视觉“颠倒”的特殊眼镜,他必须通过运动体验“娇正”他的视觉,直到他的视觉再次变成“正”的。面且,他的听觉也连同他的视觉一起被改变了:如果他仅仅听面不同时看见声音源的话他就不能充分地指出此声音源。这意味着,我们关于视觉被运动的可能性塑造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知觉。通过知觉现给我们的世界已经被身体所定向,由此,当我们看或听到世界内诸物时,我们就业已知道如何接近之。 但是,世界内的诸物,即使我们没有知觉到它们,亦是可通达的。当我在黑夜中行走时,我可能撞到树上。这意味着,即使我没有感知到它我也能通达树“本身”--尽管没有对它的感知,我对这种通达就是很自目的。然而,我可以通达物本身,仅仅是因为我已通达我的身体,身体总是由我支配的--它总是可通达的。我永远不会“盲日”于通达我的身体不是因为我总是感知它,而是因为我总是领会着移动它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之运动的恰当的“视见”。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团上眼睛,我仍能按我想要的任何方式移动我身体的任一部位。同样地,一条鱼也许永远看不到它自己的尾巴,但它仍然没有任何困难地移动自己的尾巴。当我们移动时我们总是直接地移动身体,而不用通过知觉来提前“发现”它,因为我们总是直达身体。这种对身体的直达将身体与世界内的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只有通过移动我们的身体才是可通达的。 然面,尽管有上述这种区别,在移动身体与移动世界内诸物之间并没有本质不同。例如,当我们用笔书写时,我们并不真的在移动我们的手与移动手中的笔之间做出区分,我们移动手中的笔仿佛它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这个“仿佛”不仅仅是我们的想象,它更是基于我们对运动之可能性的理解而做出的对笔的理解。我们首先把运动理解为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以使其互相相对。但我们对世界内诸物的知觉已经被运动的可能性所改变;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世界内诸物(潜在地)理解为如同我们所移动之身体的某物。这就是为何我们接近、把握和操作它们,仿佛它们是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我们没有感到世界内诸物,我们能通官们:出就是说,这些物本身作为通过移动我们的身体就可移动的某物原初地向我们开放一-它们是我们的移动的身体的延,它们是“身体(bodies人这就解释了我们对它们的知觉被运动之可能性改变的障因。总之,世界内诸物原初就是身体性的存在,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通过运动之可能性进人世界之中,而正是运动之可能性使得它们度为它们所是的物体 然面,为了证明运动之可能性建构了世界的世界性,我们必须证运动之可能性构成了世界的整体性。由于运动方向是由我们相对地移动身体的不同部分所决定的,因此就我们的身体面言,不同的方向就形成了个真正的整体,只要我们移动的身体是自我同一的,面不用管它有许多部分这一事实。我们移动的身体是自我同一的吗?身体总是我的身体,身体的这种“属我性”(mineness)属于我们对移动的身体的理解,因面属于我们对运动之可能性的理解。这种属我性意味着,当我移动时,我总是移"我自己”。也就是说,身体是自我的物化。因此,身体的自我同一就可无视身体有许多部分这一事实。这样看来,定向体系就我们移动的身体面言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这即是说,我们运动于其中的世界--在其中,世界内诸物变得可通达--在运动之可能性的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这样一个真正的整体先于对世界内诸物的发现,因为只有通过运动的可能性诸物才能进人世界并且对我们成为可通达的,因此。我们能得出结论:我们运动于其中的世界的世界性就是运动的可能性。 二 经由身体,现在我们赢获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性”概念。然面,此新的“世界性”额念不能取代旧的“世界性”概念,因为它们是两种世界的两类世界性。出界的意菌是我们所操劳的世界的世界性;运动的可性是我们在其中运动的世界的世界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既是我们所操劳的世界,也是我们在其中运动的世界。这两种世界性是如何互相结合面构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呢?世界的意蕴首要地自了…”来决定,面“为了……”并不来自世界内诸物的有用性。相反,出界内诸安对能在之所以有用,只是因为此在为自己面存在一一也就是说,这其是区为此在把他自己的存在当作一个问题而时间性逃筹划他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月此,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的生有是由,为了……’所规定的”少。然面,世界内诸物只有通过运动的可性才是可通达的,虽然对其物的知有副丁指导我们对此物本身的接近,但是,这仅是因为知觉已经被运动的可能性所改变。当我们仅仅看着某个物体,在我们对此物的理解中,运动的可能性被无视,此物导现为似乎仅仅是为了感知成沉思的某种东西,即现成在手的某种东四。上手之物与现战在手之物的本贡区别是、前者是丛运动的可能性来理解,面后者不是。可能有人会争论说,从以下事实出发亦可区分上手之物和现成在手之物,即前者是有用的,面后不是。如果我们续义地从实际有用的意叉上来理解有用性,那么现成在手之物看起来确实是无用的。然而,如果我们从规定着此在的整个生存的“为了…的角度来理解现成在手之物,那么现成在手之物也是有用的:如,它可被用于美学欣赏或理论创究,而这甚至是一个脱离肉体的意识(不拥有运动的可能性)也能为自己追求的目的。因此,只要世界是我们发现上手用具并使用它之处所、"在一世界-中”就只能是“通过-身体一在-世界-中” 其结果是,仅仅是“为了……”并不是足以把我们之生存的敞开性决定为一个世界--它可能决定着其他敬开方式,而不是我们能于其中发现上于用具并使用它的世界。为了决定这样一个世界,"为了……”必须被老银给运动的可能性,而这种指派总是已经发生,因为以移动我自己的方式移动身体是此在存在的一种方式,因此被包含在“为了……”的力量之中。此在总是为了自己而运动。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运动因此拥有着“为…而动”的形式。这不仅使诸物可通达,而且使其对此在的生存有用。因此既不是单独的“为了……”,也不是单独的运动之可能性,而是二者的结合规定了作为我们的存在方式的“在-世界-中”。由此看来,世界既是我们的操劳之地,又是我们的运动之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由于我们总是把运动理解为“为……而动”,我们的运动已被它们的意蕴所塑造。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动通常是受它们的意蕴而不仅仅是受运动的可能性指导的。例如,当我们说出一个词时,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去考虑如何按某个方向运动我们的舌头的哪一部分到何种程度。舌头的运动通过我们先前说出同一个词的经验,已经被我们想要说出的词所塑造。因此,我们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想要说出的词,它会自动引起舌头的运动。仅仅当我们学习说一个新词并且发现要说出它很困难时,我们才可能需要考虑舌头的运动,并可能用一面镜子去纠正舌头运动的错误。但说出这个新词,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受词的意义所指导的任务。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我们就可以忘掉我们已学到的关于舌头运动的知识。上述我们关于说话所说的,也同样适用于乐器演奏或者更简单的运动,如行走、吃饭、开门,等等。所有这些具体运动都受它们的意蕴引导,而不仅仅是受运动的可能性引导。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们甚至可能会失去绝大部分关于运动之可能性的理解,而只能受意蕴引导或在知觉的帮助下成功地运动。在梅洛-庞蒂关于施耐德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施耐德的大脑的某部分受到损伤之后,他不再能闭上眼睛做“抽象运动”,即与实际情境无关的运动。但是:“即使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病人也能迅速而极其有把握地完成生活必需的运动: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擤鼻涕,从火柴盒里取出一根火柴点燃一盏灯”显然,对他而言,作为一种领会的运动之可能性已经损坏,但与所有其他人一样,运动之可能性在损伤发生之前就已经塑造了他的视觉,而运动的意蕴也塑造了他的具体运动。所以,在损伤发生之后,他仍能睁开眼睛做抽象运动,即仅受运动之可能性引导的运动,但无法闭上眼睛来做。反之甚至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他也能做具体运动,因为具体运动仅仅受它们的意蕴引导,这些意蕴在他的大脑损伤之后仍然保持完好。 这个例子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当意蕴保持完好而运动的可能性损坏时在人的存在上所发生的事情一一人只能对实际处境做出反应,而失去了绝大部分自由生活的能力。“施耐德的一般智力没有受到影响”,但“他从不自发地唱歌或吹哨”。“他出门从不是为了散步,而总是为了差遣。”“他只能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交谈。”“在他的所有行为中,有某种谨小慎微和严肃的东西,这源于他无能于表演。” 总之,“他受到现实的'束缚’,他'缺少自由’,缺少作为适应处境的一般能力的一种具体的自由”。这种“具体的自由”,如果我们根据上述分析来理解它,就建立在以我们想要的任何方式来移动身体的可能性之上。 因此,这个例子表明,在运动之可能性与“在-世界-中”的自由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联系。让我们试图使这种联系更清晰一些。由于“在-世界-中”被“为……而动”所规定,因此“在-世界-中”的可能性就可被分解为运动的可能性和“为了……”的可能性,后者包含这样一些可能性,如为了艺术的可能性、为了哲学的可能性、为了爱情的可能性、为了生存的可能性,等等。我们总是能向着这些可能性筹划我们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筹划总是能对我们敞开这些可能性。然而,考虑到在世界中存在由“为了……”的运动所规定,那么,只有从运动的可能性出发来理解以及通过运动的可能性来执行时,“为了……”的可能性才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例如、人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画家,而不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只有当人们将此选择转化为身体移动的具体方式时,该选择才是一个实在的选择,如拨通了一所美术学校而不是一所音乐学校的电话,去一个卖绘画材料而不是音乐器材的商店,学习使用钢笔和剧子而不是在乐器上练习手指。总之,一种新的“在一世界-中”的可能性,只能作为移动身体的一种新的方式来得到发展,直到它成为习惯。当人们对运动可能性的理解遭受提伤(如施耐德的情形),人们就只能按照唤醒人们的习惯性反应的实际处境的意蕴面行动,却不能同时看到许多不同的行为方式--只有当人们当下明白了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移动身体的可能性时,这些行为才能被理解为当下的真正可能性。因此,可以说,运动之可能性建构了“在-世界中”的基本自由。 总结上述有关两种形式的世界性的讨论,就此在的生存被一种时间性筹划的“为了……”所规定面言,在决定世界为此在筹划自身之何所向方面意蕴比运动的可能性更为源始。然面,正因为此在是身体化的,它才向一个它可以在其中通达诸物的世界开放。这样一个世界同时是一个意蕴整体,因为“为了………”将运动归人其自身的力量之下,并且把后者转化为“为面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在把我们的存在的开放性规定为一个世界这一点上,运动的可能性比“为了……”更为源始。最后的结论就是:在构世界现象的过程中,两种形式的世界性同样源始且互相依赖。
三 身体在建构世界现象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是的,因此很难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在《存在与时间》中考察世界的世界性时忽略了它。人们可能会争辩说,身体是隐含在海德格尔的思考中的,例如,在上手状态中对“手的使用。但对身体存在的这种影射只是更清楚地表明,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身体现象,但与此同时又故意避免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人们也可能会争辩说,在海德格尔将其视为意蕴的“世界性”概念中,运动已被纳入考量;例如,他把“锤打”描述为与锤子的因缘。确实,海德格尔将“锤打”作为一个例子来表达此在与上手用具的某种因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以下事实,即这里涉及的运动仅仅是赋义整体的一个环节,而且规定世界本质结构的不是实际运动,而是运动的可能性--在我们能够接近、把握和操作世界内的任何个别事物之前,就运动的可能性而言,世界就已经是一个真实的整体了。更仔细来看,这个真实的整体甚至先于用具的整体性因为用具的整体性是由我们的安排形成的,只有当我们周围世界的诸物就它们的可通达性而言已是一个真实的整体时,这种安排才是可能的。事实上,“为了……”仅以最一般的方式规定了世界的意蕴整体,而实际性地形成作为意蕴整体的世界取决于我们自己。但就运动的可能性而言,世界永远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除非这种可能性受到了损坏。 让我们回到施耐德这个例子。先前的分析表明,病人对运动之可能性的理解受到了破坏,但他对意蕴的理解保持完好。那么,他的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呢?“在他的情况下,可能的处境在任何时候都十分狭小,以至于环境的两个不具有任何共性的区域无法同时构成处境。如果人们和他交谈那么他就听不见隔壁房间里的交谈声;如果人们把一盘菜端上桌子,那么他绝不会问这盘菜来自何处。”似乎他的环境的整体性破碎了,因为他只能依靠意蕴来理解他的环境,而环境中的物并不总是以意蕴的方式相互关联正常人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论环境中的物相互之间在意蕴上多么不同它们总是处于一个自我同一的整体--我们在其中运动,并通达世界内诸物的世界--之中。 有证据显示,海德格尔实际上已意识到了两种世界形态的区别。在他1929-1930年的讲座中,他提出,“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的世界是贫乏的,而人是构成世界的”。他承认,如果人们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者的可通达性,那么“人和动物一样拥有世界”。但是,由于只有人能把存在者当作存在者来理解,面动物并不处于存在者的显现之中,因此动物根本没有世界尽管这种“没有”是建立在拥有开放性基础之上的。2海德格尔的考察最后得到这样一个“世界”概念,即“存在者作为自身和作为整体的显现”它由我们的筹划,即由我们的构成世界所规定。四在这里,重点又一次被放在了世界的意蕴上。当海德格尔讨论存在者的可通达性时,身体现象还是未获专题研究,仅作为一个尝试性的“世界”概念被引人,并因其好“存在物的显现”而被否定。 但即使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已暗示,他将在稍后处理关于身体现象的问题。在他考察“世界的世界性”的第三章,他试图用一部分内容依世界的意蕴(而不是运动的可能性)来解释空间性。但当他讨论左和右的方向时,他遇到了身体问题:“此'身体性”隐藏它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准备讨论它。”他略示并预期的对身体的讨论推迟了近4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为一群精神分析学家举行的措利孔讲座中才最终拾起。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试图考察许多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已经分析过的身体现象,尽管海德格尔似乎不了解梅落-蒂的工作。完全靠他自己抵达了这些现象。这里,我们不打算列出这些现象的清单,因为本文所要做的仅是理解身体与世界的本质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打算聚焦于海德格尔的“身体化”(Leiben)这一概念,它似乎最能使我们理解这一关系。 海德格尔首先通过考察当前化现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指出,当讨论会的参与者呈现(当下不在场的)苏黎世中央火车站时,每一个讨论会的参与者都面对火车站不同的面,但所有人呈现的都是相同的火车站,即火车站“本身”。类似地,“我们看物,例如这个碗和这本书,只是从某个特定的方面看,然而我们'看见’并意指的是整个碗、整本书”。在此,我们所通达的物“本身”以及这种通达改变了我们的视觉这一事实似乎呼之欲出。通达物,即是我们对它们开放,“对所呈现的东西保持开放是人的基本特性,但对存在的开放包含着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直接接触那些影响我们的身体的物,是所有开放的普遍方式”。然而,我们亦能对遥远的、并不物理地呈现的物保持开放,例如那个火车站。“如果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和不能做到,那么,举例来说,今晚你永远不能回到家里。”因此,不是知觉本身使我们向存在者开放,“因为我永远不能驾车去往一个单纯的意象”。虽然关于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向远距离的、不能物理地呈现的物开放,且又最终使我们物理性地到达它们,海德格尔并没有讲清楚,但相当明显的是,运动的可能性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当前化的讨论的结尾,海德格尔声明,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我们遗漏了身体”;因此,在接下来的讲座里,他将处理身体问题。 为了厘清我们“在此处”但又同时“在那里”与远处的物相处的现象,海德格尔区分了物的界限与身体的界限:“当我用手指指向那边窗户上的开关时,我的身体并不止于我的指尖处,那身体的界限何在呢?”“身体向来总是我的身体。”由此可推导出,身体化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且“在入迷逗留于显现的存在物的意义上,由我的作为人的存在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此在时间性的筹划敞开了一个领域(当前)。在此领域,此在可逗留于向之展开的诸物之中,并且此在的这一存在方式--时间性--共同决定此在身体化的界限。在此,海德格尔似乎将“此在为它自己存在这一实情和“身体向来总是我的身体”这一实情联结了起来。“身体化具有对自我(theself)的特殊关系”,以至于当我移动时,“我移动我自己”。回想我们先前的讨论:身体的属我性使得运动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实的整体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身体化的界限就是运动的可能性。然而因为“为了……”支配了运动并将其转化为“为……而动”,所以身体化的界限实际上是由运动的可能性和“为了……”的结合决定,亦即由完整意义上的世界的世界性决定的。这种世界性规定了世界“在-世界-中”之可能性的整体,而此在则依后者筹划自己。 因此,海德格尔说:“身体化总是属于'在-世界-中’。它总是共同规定着“在-世界-中’、开放性及拥有一个世界。”这种规定是一种与意蕴的共同规定。“在我指向窗户的开关时,身体化视域延伸到所感知与所见之物。但在身体化本身中,我不能体会到任何关于窗户开关本身的意蕴。”因此,“在-世界-中’本身是一种身体化,但不仅仅是身体化”、“我们所有的生存行为,必然是一种身体性行为,但不仅仅是身体性行为,它本身就是身体性的。然而,生存必须事先就被规定为与世界的关系。”至此,重点又一次落在了意蕴上。但海德格尔似乎接近于宣称,世界的本质结构由意蕴和身体化共同规定。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按运动之可能性发展“身体化”概念,但身体在建构世界现象中的作用基本上已映入眼帘,他先前对此作用保持沉默的原因,在他对萨特的责备的回应中变得清晰(后者对他在整部《存在与时间》中仅仅用六行书写身体感到困惑):“我只能如此反驳萨特的责备,那就是指出,身体性是最难以领会的,在当时我不能够说得更多。” 在《存在与时间》中不能“说得更多”的东西,他在措利孔讲座中说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措利孔讲座使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世界性的考察更完备了,可以被看作对后者的一个补充。
|